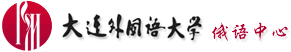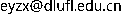啊,
伟大的、有力的、真实的、自由的
俄罗斯语言啊!
屠格涅夫《俄罗斯语言》
纳博科夫认为:“对于(俄罗斯)这个没有任何文学传统的民族的文学创作而言,一个19世纪就足够了,它不仅有自身独特的艺术价值,也有世界性的影响,除了数量上不能与英国、法国文学相提并论,它在任何方面都可以与这二者比肩,尽管这两个民族创作文学杰作的时间是那么久远。”这位一手用俄语创作诗歌,另一手用英语撰写小说的俄裔美籍作家何以能拥有这份满满的自信?
此外,提及19世纪俄罗斯诗歌,除了普希金,中国的诗歌读者还知道什么人呢?或许,由问题带出的结果,将是对俄罗斯诗歌的全面了解和全面评估,也是认识上进行积极调整、趣味加以适当改变的一个契机。在19世纪俄罗斯诗歌的天空上,普希金并不是一颗孤独的太阳,与他一起闪耀的至少还有茹科夫斯基、巴拉廷斯基、丘特切夫、莱蒙托夫、柯尔卓夫、波隆斯基、费特、迈科夫、涅克拉索夫和尼基丁等灿若星辰的名字。
自从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将人类划出了“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黑铁时代”等分类之后,后人就以一种怀古的情愫来追忆和想象他们已逝的美好时光。有意思的是,由此衍生了非当下的命名,某种饶有趣味的“追认”现象。在俄罗斯的诗歌史上,“追认”也一再出现,正如近年被人们广泛谈论的“白银时代”这一名称并不出现在那段文化的鼎盛期,所谓的“黄金时代”也是由它的继承者追封的一个“谥号”。据说,有一次,一批诗人在阿赫玛托娃家聚会,大家不满当代文学的现状,认为那时的俄罗斯处在精神的整体衰落状态,讨论与经典和传统之间的关系,对19世纪诗歌流露了羡慕与推崇的意愿。儿子列夫在旁边插了一嘴:“你们如此向往普希金的时代,将它称之为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代,那么,你们就是白银时代了?”这个传闻一度被当成俄罗斯文化“白银时代”之命名的由来,虽然它实际并不准确,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后人对以普希金为代表的一个诗歌时代的肯定与重视。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儿子创造了老子,“白银时代”的一辈,向“黄金时代”的父辈乃至祖辈投去了恰如其分的敬意。
茹科夫斯基从古典主义占据主流的诗坛为俄罗斯诗歌开辟了一条独特的路径,让写作越过了僵硬的规则和定律,赢得了创造的优先权。著名的批评家别林斯基认为,茹科夫斯基对俄罗斯文学“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他是发现了诗歌新美洲的水手“哥伦布”,“没有茹科夫斯基,就没有普希金”。另一位诗人巴丘什科夫则在形式上做了更多的探索,他是“诗的语言的革新者”,努力为俄罗斯诗歌“创格”;与此同时,他的天性又“包含着古希腊精神的因素”,“与古代世界发生共鸣”,这让他的诗歌拥有了某种经典性的品格。
巴拉廷斯基是著名的哀歌诗人,他声称“对时间而言,我微不足道,但对自身而言,则意味着永恒”,为此,他刻意表现一种“沉思的忧郁”。巴拉廷斯基擅长心理分析和抒情思考,注重在诗歌中处理戏剧性的内心冲突,在简洁的文字中摹写丰富的精神世界。他的作品有着强烈的预言性,《最后的诗人》的开篇以先知的口吻揭开了工业文明繁盛后带来的弊端和功利性的价值观的肆虐,不能不令人感到一种惊悚感:“世界沿着钢铁之路向前迈进/利欲熏心,与日俱增,/大众的梦想越来越明显地关注/急功近利的事物,愈益无耻。”
诚然,普希金这个名字(实际是姓)在俄罗斯可谓家喻户晓,无论是在专业的诗人圈,还是普通的读者群,他已成了民族的骄傲,几乎被看作缪斯的男性化身,不同的只是他披上了一件俄罗斯的民族服装。果戈理认为,普希金就“像一部辞典一样,包括着我们语言的全部华美、力量和柔韧性”。在创作上,他善于使用新的词汇,避免豪言壮语和老生常谈的流弊,同时还“赋予老字眼以新的生命”,营造了一个繁复多样的世界。此外,尽管诗人不断遭受到命运的打击,他在创作中也一而再、再而三地触及死亡、痛苦、孤独、绝望、悲伤等主题,然而,他都以自己旺盛的生命力将它们内化为新的力量,在诗意的层面上加以提升,使之成为“明亮的忧伤”“痛楚的甜蜜”“绝望背后的希望”“死亡之后的新生”,这些都非常贴近我们当代人的行为选择,更是一种面向未来的人生观,它们体现了一个经典诗人超前的现代意识。
在俄罗斯诗歌史上,丘特切夫与普希金堪称双璧,他俩各自划出并延展了不同的方向。有意思的是,普希金还是丘特切夫的“伯乐”,他首先将后者的作品题为《寄自德国的诗章》,发表在自己主办的《现代人》杂志上,为当时尚默默无闻的诗人提供了重要的发声机会。作为俄罗斯诗歌的抒情思想家,丘特切夫的创作无疑有着显著的哲理倾向,他善于将人生观和宇宙观寄寓于风景的素描中,而从情感的抒发中追问生命的意义,我们在他的作品中随处可以遇见人格化的自然和自然物的人性。诚然,丘特切夫的诗歌绝不是德国哲学的简单翻版。与他同时代的小说家屠格涅夫对丘特切夫的诗歌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他的诗歌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它们就像包孕在语言中的火星,受到了情感与印象的刺激而被点燃,因此,“他的思想对于读者从来不是赤裸的、抽象的,而总是和来自心灵或自然界的形象相融合,不但深深浸透着形象,而且也不可分地、连续地贯穿在形象之中”。托尔斯泰可以背诵诗人的不少诗句,声称:“没有丘特切夫就不能生活。”
19世纪中叶,俄罗斯诗歌形成了两个较有影响的群体——“普希金诗歌圈”和“丘特切夫昴星团”。它们有点类似于中国词坛上的“豪放派”与“婉约派”。颇有意思的是,“普希金诗歌圈”的诗人大多具有“横放杰出”的气概,他们对社会、对现实负有天然的使命感,其审美的敏感往往叠加了强烈的公民意识。属于这一群体的是一批十二月党人,雷列耶夫、丘赫尔柏凯、德尔维格、奥陀耶夫斯基等。尽管这部分诗人出身于贵族的居多,却并不妨碍他们关注民间,尤其是对俄罗斯民歌的吸收和改造,这使他们的创作始终拥有肥沃的土壤,并洋溢着蓬勃的生命活力。
归入“丘特切夫昴星团”的诗人大多推崇唯美主义的“纯艺术”倾向,在创作上的共同理念是对美的崇拜和哲理性的追求,整体诗风恰可对应于中国的婉约词,显得“辞情酝藉”“宛转柔美”,在隐约、曲折、精细、隽秀中凸显微妙、含蓄的诗意。更有意思的是,其中一部分诗人也擅写“闺情丽思”,不时绽露旖旎、柔婉的风情。它的代表诗人除丘特切夫以外,还有维雅泽姆斯基、格林卡、霍米雅科夫、舍维廖夫、雅库博维奇、别涅季克托夫、费特、迈科夫、波隆斯基等。需要说明的是,对美的无限崇拜也来自古希腊人对世界的认识,帕纳斯山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存在。俄罗斯人一直就认为自身是希腊文化最正宗的继承者,因此,某些非本土的“舶来”文化颇有意味地获得了较为适宜的嫁接,成为民族脉管中流动的新鲜血液。
19世纪五六十年代,涅克拉索夫主编的杂志《现代人》和《祖国纪事》在俄罗斯人的精神生活中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他的诗神不再关注玫瑰、夜莺和月亮,而是一位在“生活的田野”上漂泊的“被鞭笞的缪斯”,揭示着时代的堕落和专制制度的残忍。他的诗歌在抒情的基质上增加了不少叙事元素,增加了诗歌对现实的介入与批判。同时,它的衰态也非常明显,一部分作品流于简单和肤泛。这一弊端到了他的模仿者那里,就变得更为突出,诗歌被散文化、口号化,甚至意识形态化。俄罗斯民众之生活的苦难虽说得到一定的揭示,但其中的审美魅力也不无遗憾地有所丧失,一部分作品无论在结构还是语言上都显得较为粗糙,语言的润滑度也因此被消耗掉了。在一定程度上说,涅克拉索夫堪称黄金时代最后一名具有黄金歌喉的歌手。1878年,他的去世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
(文章来源:网易新闻)